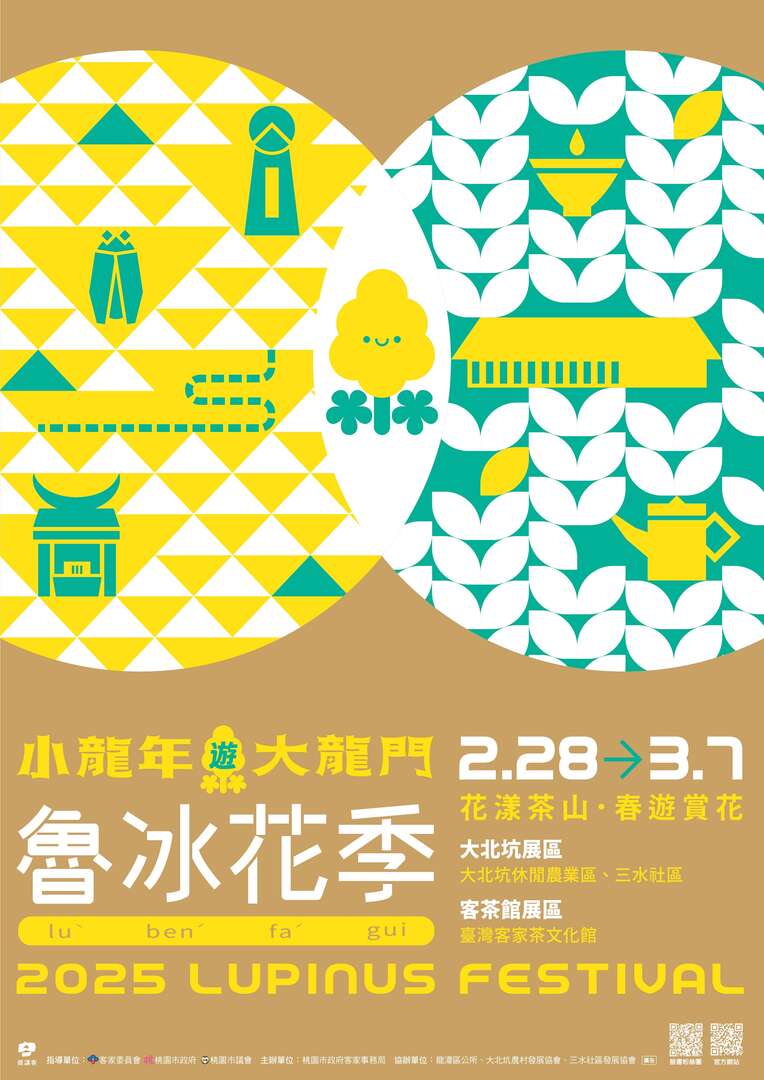【文稿由通識教學部 傅子耕副教授提供】
生活重心從西歐城市轉往中歐的過程是辛苦的、繁複的。在完成轉移的前半年,我去了幾個城市,在最後一個月時,我們橫貫中西歐,並以維也納為折返點,繞了中西歐一小圈,回程沿著重要的阿爾卑斯山脈自然屏障回到了西歐/中歐城市洛桑。阿爾卑斯山脈自然屏障開啟了瑞士邦聯的周圍領地,可謂:「若無阿爾卑斯山脈,就無瑞士。」與其緊鄰的是,奧地利、義大利與瑞士。以維也納為起點往西,沿路經過薩爾茲堡、茵斯布魯克,一路可以抵達瑞士邊境。這一條通往西歐之路,也讓瑞士與奧地利的地位不同於其它國家。然而。奧地利的歷史背景以及它們二戰、一戰後的戰敗命運使得這兩個國家的前途截然不同。
雖然說,奧地利人可以不算是日耳曼人,但有了合併至「祖國」德意志的過往加上使用德語的緣故,讓奧地利難以擺脫日耳曼民族的刻板印象。瑞士70%的人口也使用德語,但由於未被希特勒入侵,似乎讓瑞士持續保有其該有的樣貌,大家也不大有日耳曼民族的這種刻板印象。
奧地利納入納粹德國前,稱為奧地利共和國,是奧匈帝瓦解後的產物,同期的還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波士尼亞與赫賽哥維納等等。然而,該區域在帝國瓦解後,仍以維也納為中心;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心則是布拉格。當時,作為非歐盟居民,在辦理入境捷克的工作居留簽證時,除了到台北商務辦事處辦理之外,在歐洲得要前往駐維也納的該國大使館辦理。若沒記錯的話,再加上2024年初的這一次,我應該來過維也納六、七次,當然,不是每次都是為了簽證。

(捷克布拉格美景/照片由本報訊提供)
弗洛伊德家鄉—夢之都維也納
我很喜歡維也納,適當的規模和人潮,古老的地鐵和路面電車,無數的咖啡館,還有胡亂說德語的機會。印象中除了開車那次之外,我都是搭飛機去,噢,不!還有一次為了能夠免去轉機,享用直飛桃園機場的機會,選擇了從捷克搭著很慢的火車到了維也納。我也對維也納的機場有好感,這次再去也沒有失望。離開歐洲將近十年,原以為早與維也納絕緣了,但拜這次參訪所賜,我又降落了維也納機場。從維也納機場進入市中心的難度很低,從質樸景色一路變化到環城電車,入城所及之處無不是古典風味,皇城的過往更讓維也納不凡。
我雖然沒有真正居住在維也納和布拉格這兩座奧匈帝國古城,但二十世紀的人文社會情勢和學術發展使我嚮往成為這座城市的一部分。除了各項城市特色之外,最初讓我和維也納相連接的是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邏輯學家哥德爾(Kurt Gödel ),還有在歐洲才開始真正認識的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我看這次就先不談哥德爾了吧!弗洛伊德的看診間(房子)在維也納大學後面,我一直藉著前往維也納聖誕市集的印象理解它的相對位置,沒有機會去那參觀。這回,我想著:「無論如何都要去那裡參觀」。但是,我又失敗了;相反地,我「只是」在那附近的維也納大學走了一圈,但這經驗卻比我想像的更好、更值得。兩年前準備「歐美文化與文化創新產業」這們課時,我查閱了幾本書,以便從我的記憶中找回這些埋藏多年的資訊。關於德語世界的部分,我常參考蔡慶樺博士的作品,2021年《維也納之心:疫情時代的德語筆記》彌補了我缺的維也納生活經驗,這本《維也納之心》以短文的形式呈現,書中有很多現成的知識,節省我不少的備課時間。例如,佛洛伊德故居位於Berggasse 19, 1090 Wien,現為佛洛伊德博物館、佛洛伊德公園是佛洛伊德經常散步的公園等等。幸運的是,這次我在維也納拜訪了作者本人,他是現任駐奧地利台北經濟文化辦公室第一秘書(Erster Sekretär)。一起在司法宮午餐後,蔡博士為我們一行人做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史蹟導覽,很多都是和維也納圈相關的故事,悄悄地讓我串聯了這些年所有的讀書經驗。

(維也納熊布朗宮/照片由本報訊提供)
天才維根斯坦的家鄉
在大時代的背景下,身為猶太人,要能夠離開而前往倫敦度過餘生者,並不多見。佛洛伊德在當時早已名滿全球,英國可以說是展開雙臂擁抱他一家人。相似的重要人物還有維根斯坦。其實,在和維也納藝文相關的書籍中會論及維根斯坦者,或許遠不及提到克林姆(Klimt)和百水(Hundertwasser)的機會。但是,從雷伊・孟克(Ray Monk )《天才的責任》一書中,我們清楚看到他在藝文上的品味;談到維根斯坦的生命,音樂與藝術就變得相當重要,不僅平靜他的心也直接形塑他對哲學的看法。而他由此而衍生出的哲學思想,確實也對時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今,難怪描寫二十世紀「智性發展史」的《現代心靈》一書中,就在書中的第一部分以佛洛伊德為始,並以維根斯坦為終了!
維根斯坦出生於維也納,父親是世界知名的鋼鐵富豪,一家非常富裕。在一戰期間服役時,維根斯坦曾被同袍問及是否是那個維根斯坦家族成員,僅因為克林姆替他姐姐畫了一幅當時知名的肖像畫。在這個家族的發展過程中,許多重要的音樂家和藝文人士都和維根斯坦一家往來,間接地養成維根斯坦的音樂素養、型塑出他對物品獨特且高雅的品味;維根斯坦甚至還有建築設計,目前仍留於維也納當地做為保加利亞駐維也納大使館的文化部使用。身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的哲學儘管沒有明說,但跟這些都脫不了關係,算是能與當時的現代主義建築的精神相契合。戰爭後,維根斯坦回到劍橋,經濟學家凱恩斯(Keynes)說:「呃,神到了,五點十五分的火車,我接到他了!」凱恩斯所指的人便是維根斯坦。
文化藝術生活匯集處—維也納的咖啡館
整個維也納就是一座Café城,二十世紀的維也納思潮:藝術、文學、科學、分析哲學,以及歐陸哲學等等,可以說是奠基於此種Café文化。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當時匯集了相當數量的維也納藝文人士,地址是Herrengasse 14, 1010 Wien,搭乘U-Bahn, U3步行可抵達。維也納咖啡文化於2011年起,列為UNESCO非物質遺產。 一直以來,都有一位看似藝文人士的雕像坐在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門口,他到底是誰呢?絕對不是我認識的當代哲學家,那想必會是一位重要的文學家吧!讀《維也納之心》解答了我一直以來的疑惑,奧地利作家彼得・艾騰貝格(Peter Altenberg)因為常去這間咖啡館,甚至將他的收信地址寫在這間咖啡館,於是出現了「如果我不在家,就是在咖啡館;如果不在咖啡館,就在往咖啡館路上」這句名言(原文: “Wenn der Altenberg nicht im Kaffeehaus ist, ist er am Weg dorthin" )。艾騰貝格過世後,咖啡館替他做了雕像,讓他至今仍坐在店內。
一百多年來,有一種由咖啡文化產生的連續性在歐洲大陸生成,我想這些咖啡館仍會是我未來介紹維也納的起點,佛洛伊德常去Café Landtmann,但克勞斯(Karl Kraus)、茨威格(Stefan Zweig)、馬薩里克(Thomas Masaryk)、克林姆(Gustav Klimt)、埃貢・席勒(Egon Schiele)、阿德勒(Alfred Adler)、婁斯(Adolf Loos)都跑中央咖啡館,印象中還有更多知名人士!維也納學派、維也納大學、佛洛伊德、哥德爾與維根斯坦,中央咖啡館,一起構築了我對二十世紀的哲學介紹開端,然而對學生而言,維也納這座城市仍是太遠了一些,而我知道的也仍舊不足。

(中央咖啡館/照片由江鴻津提供)
世紀末維也納文化成就的連結為何?
在三民書局出版的《奧地利史:藍色多瑙國度的興衰與重生》一書中的第14章談到了奧匈帝國解體至德奧合併之間(稱為「戰間期」)的奧地利文化成就,分為文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音樂、大眾通俗文化、建築、自然科學。這一種分類的方式,一方面凸顯戰間期對奧地利的文化成就版圖之梗概,二方面可以補充自然科學(或是說科學)對當時的關鍵之地位。尤其是在,哲學、心理學,與科學之間的緊密關係。整體而言,一種「缺乏集體自我認同感」,實實在在刻畫了許多作品的特色,也反映大帝國過渡到小共和國的調適問題。尤其是,再次更換了國籍,對幸存的奧地利人而言應該是五味雜陳,一部分人成為因為德軍而再次強大,一部分只是遙想維也納;若他們不僅是單純的納粹受害者,那麼在世紀末(Fin-de-siècle)時,他們又是誰?維也納又在哪呢?

 正體中文
正體中文  English
English